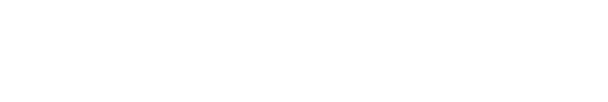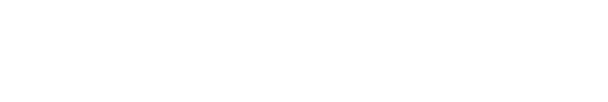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序言中指出,他和马克思“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的知识”,而“马克思是精通数学的,可是对于自然科学”,他们只能“作零星的、时停时续的、片断的研究”。而恩格斯“零星的、时停时续的、片断的研究”所形成的论文、札记等未完成的手稿,1925年以《自然辩证法》的书名用德文和俄文对照的形式首次全文发表,自然辩证法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自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传播以来,《自然辩证法》已经逐步从一部手稿发展成一门内容丰富的综合性学科,涉及疆界已从自然观、科技方法论、科技与社会(STS)扩展到现代西方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技社会学、科技伦理学、工程哲学等广阔领域。然而,在自然辩证法的版图愈来愈大之际,以西方范式为圭臬的科技哲学却令人不安地不断“蚕食”着经典自然辩证法领地,其研究距离恩格斯的基本精神越来越远。在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之际,人类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兴科技带来的颠覆性革命不仅给社会政治经济带来了全新的挑战,而且使哲学迎来了革命和重构的契机,当我们以新时代精神重新解读恩格斯的理论遗产,欣喜地发现经典自然辩证法依然是解释复杂多变的自然、把握波澜壮阔的当代科技革命乃至走出生态困境的思想指南,更是当代科技哲学的“活水源头”。
自然观的“哥白尼革命”
如果说,康德实现了哲学认识论的“哥白尼革命”,那么可以说,恩格斯实现了自然观的“哥白尼革命”。自古希腊以来,西方哲学就执着于追求永远不变的“存在”,物质世界变动不居的现象不过是“幻象”而非真实,真正的世界在本质上是静止的、永恒的。虽然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然而,即使伟大如牛顿,依然难逃“世界亘古不变”的古老形而上学观念。在牛顿经典力学的解释框架中,世界不过是一台制作精妙的机械,遵循着既定的、可计算的轨道周而复始地运转,时间仅有物理学上可计算的意义,却无任何发展的历史意义。如恩格斯所言:“不管自然界本身是怎样产生的,只要它一旦存在,那么它在存在的时候就总是这个样子。”
然而,理论不可能永远对变化这一事实视而不见。从19世纪中叶开始,细胞学说、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以及生物进化论的发现,为人类开启新的世界观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基础。恩格斯敏锐地意识到这些科学发现的革命性意义,全面总结和概括了自然界和自然科学中的辩证法问题,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新的自然观就其基本点来说已经完备:一切僵硬的东西溶解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恒存在的特殊的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然而,辩证法并非简单的方法论,而是客观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的统一,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体现了自然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它打破了传统“非此即彼”以及“亦此亦彼”的形而上学观念。自然辩证法并非如黑格尔那样把辩证法的规律硬塞进自然界,而是对自然界中抽象出来的一般规律的反映,扭转了被传统哲学颠倒的“理论和事实”的关系,以回归生活世界的精神为人类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全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唯物史观中的人与自然
恩格斯打破了西方世界长达两千多年的形而上学自然观,然而西方学界似乎对于恩格斯的这一革命性贡献视而不见。他们承认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他们认可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他们赋予波尔“共生互补”理论崇高的敬意,现象学更是成为20世纪的思想运动,唯独恩格斯被视而不见,偶有提及,也被认为歪解了马克思的思想而大加鞭笞。比如A.施密特在《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中指责恩格斯“超出了马克思对自然和社会历史的关系的解释范围, 就倒退成独断的形而上学”。马尔库塞更是认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绝对的反哲学的、机械主义的解释”。质言之,在他们看来,恩格斯“见物不见人”,是典型的自然和物质决定论者,完全背离了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精神。
姑且不论马克思是否是西方学者所谓的“彻底的人道主义者”,就恩格斯的文本来看,不仅没有忽视人的存在,而且处处表现出对人的关怀与尊重。近代以来,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的宣言改变了人顺从于自然的传统观念,使人一跃成为自然界的主人,但无论人是主体还是客体,都蕴含着自然与人之间是主—客对立的关系。马克思关于“自然史和人类史彼此相互制约”的思想,明确指出了人与自然之间浑然一体的关系,纠正了由来已久的观念。与马克思一脉相承,恩格斯严厉批评“自然主义的历史观”,指出“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在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恩格斯认为,传统的自然科学与哲学忽视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前者“只知道自然界”,后者“又只知道思想”,从而造成了人与自然之间不可弥合的鸿沟,实际上,“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与此同时,“只有人才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因为他们不仅变更了植物和动物的位置,而且也改变了他们所居住的地方的面貌、气候,他们甚至还改变了植物和动物本身”。正是基于这一基本认识,恩格斯明确提出了“今天整个自然界也溶解在历史中了”的正确论断。
没有自在客观与人无涉的纯粹自然,自然与人须臾不可分离,自然总是打上了人的烙印的自然;人则总处于“世界之中”;自然是人“无机的身体”,人则是自然的“有机身体”。从而,长久以来被神秘化的意识,也不过“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这里不言而喻,归根到底也是自然界产物的人脑的产物”。恩格斯对于自然的探讨,实际就是对人的探讨,因为人与自然不可分割,他对于自然科学的深切关注,饱含着对于人的深情。在人与自然关系相对恶化的今天,重温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相统一”的论断,深入研究“人工自然”“生态伦理”以及“生态文明”,既有助于继承和发扬恩格斯的自然观,又能够为人类走出生态困境提供理论上的启示。
科技服务于人类
人就在世界之中,要时时刻刻与周遭世界打交道,打交道的过程就是生活。而所谓生活,无论个人还是民族,其存在的前提是物质生产,生产的水平决定了生活的水平。对于物质生产而言,一个重要的决定性要素就是生产工具,即物化的技术。技术发展的程度决定着人们的生活水平,在这个意义上,技术蕴含着实现人类幸福生活的“善”的功能。
近现代以来,自然科学尤其是技术的发展,使人类走上了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快车道。面对这一前所未有的景象,年轻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感叹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的确,社会的发展似乎实现了启蒙思想家们所期待的理性“千年王国”,黑格尔的话充分表达了这一乐观情绪:“人获得了自信,信任自己的那种作为思维的思维,信任自己的感觉,信任自身以外的感性自然和自身以内的感性本性;在技术中、自然中发现了从事发明的兴趣和乐趣。”进步与乐观成了这一时代的基本情调。然而,私人所有制所产生的异化劳动带给个人和劳动者的并非快乐与幸福,相反,随着工业(技术)对自然力的应用和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工人的生存状况却不断恶化,过度劳动日益增加,群众日益贫困,劳动者不断丧失自身的价值而“被贬低为动物”。技术进步了,物质丰富了,工人的处境却更加恶化了,科技的发展并没有带来人们所期待的理想福祉,机器反而成了工人们日益厌恶甚至意欲摧毁的枷锁。究竟如何审视技术的限度?技术如何才能为善?
面对技术异化,恩格斯并没有留恋前工业时代的生活。固然,在大机器生产出现之前,自给自足的纺织工在家里,以自己的手工劳动进行相对散漫自由的生产,他们有微薄的收入,还可忙里偷闲到园子里和田间锻炼身体,或者与邻居一块儿娱乐和游戏。然而,在恩格斯看来,纺织工人的这种生活虽然“很理想很舒适,但到底不是人应该过的”,因为归根结底“他们那时也不是人,而只是一架替从前主宰着历史的少数贵族服务的工作机”。工业革命的到来“促使这种情况达到顶点,把工人完全变成了简单的机器,他们最后剩下的一点独立活动的自由都剥夺了”。物极必反,如果说工业革命让人们体验到了最残酷最痛苦的生活,那么,这种生活也让人们开始反思技术和机器的限度以及机器生产走向“善”的可能性。恩格斯就此指出:“如果说机器也给工人带来某种好处,那只是它向工人证明了社会必须改造,使机器不再为害于工人,而是造福于工人。”
如何使技术不再危害人,进而使技术造福于人类?恩格斯不是从微观技术本身探讨其存在的技术缺陷,而是将技术作为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指出技术异化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大行其道的资本逻辑把剩余价值看作生产和交换的唯一动力,进而以私产制度和资本为基础,建构了可以获取巨大剩余价值的现代技术体系,而无视技术发展引起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也即生态恶化与贫富差距。如果要想克服这些问题,仅仅“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的一致”是不够的,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和马克思一样,恩格斯强调“只有消灭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技术异化的社会根源。只有共产主义这种“能够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像一般生产曾经在物种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质言之,制度变革与社会改造是消除技术异化的根本方式。这意味着,新时代大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既是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理论遵循,更是让技术服务于人类美好生活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