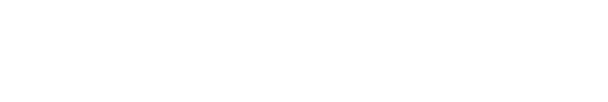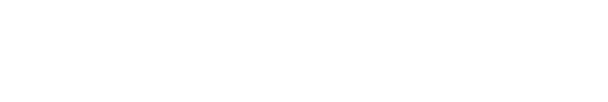重思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哲学的关系问题研究,尤其要直面如下问题:如何基于《资本论》重释马克思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差异性?如何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为此,本文尝试从三个维度对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哲学关系研究进行反思。
重思研究方向
当前,关于马克思与西方政治哲学家传承关系的研究日益深入,但对二者间发展关系的研究却明显不足。对此,研究者必须直面如下问题:马克思在何种意义上是近代政治哲学传统的继承者?何种意义上又是其超越者?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当代研究应该更关注二者之相似性和连续性,还是二者之差异性和变革性?关注二者之同带给我们什么,关注二者之异又能给我们开启什么?
从思想史诠释来看,比传承性或连续性更为重要的是传承中的发展点或差异性。阶段特定性是历史唯物主义内在历史性维度的关键。正是对历史的特定性、历史性的定在的反复探究,真正彰显了马克思思想的历史深度与复杂性。如果将《资本论》定义为政治哲学思想史的一个阶段,那么更重要的不是近代政治哲学、政治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连续性,而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之所以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对于近代政治哲学的差异性。
从《资本论》的阐释性研究本身来看,阐释不能停留于从前人或他者角度言说马克思自身,也不能停留于将前人、他者与马克思简单比附,而应该从马克思自身言说中去发现他者的位置。也就是说,不应仅仅关注《资本论》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异中之同,而应更多关注二者的同中之异。研究应该经历下述三个阶段的发展,才能深化。首先,“从自身直接言说他者”即简单地立足于所谓“基本原理”去单纯否定近代政治哲学。其次,“从他者反思地言说自身”即立足于思想史连续统从近代政治哲学去观察和比附马克思。最后,“从自身再生产出他者”即立足于《资本论》自身语境,将近代政治哲学从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内在地再生产出来。由此,才能更为具体地把握马克思与西方政治哲学间的历史性关联。
从这种意义上说,研究马克思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关系也应遵循“从后思索法”。也就是说,不是按照自然时间顺序先后继起地、外部并置地理解二者关系,而是从作为当下语境的《资本论》出发,回溯近代政治哲学,发现近代政治哲学的内在矛盾、内在批判趋势,进而向未来预见展望政治哲学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的重新奠基与理论升华。由此,《资本论》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关系,就打破了“过去—现在—未来”的线性时间诠释关系,而走向一种立足《资本论》的共时性逻辑关系。只有突破了思想史诠释的线性模式,才能从诠释走向理论建构。要言之,关注二者的异中之同,导向的是思想史诠释;关注二者的同中之异,则导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自觉以至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建构。
再探研究内容
研究方向的转换最终要落实到研究内容的深化上。从上述思想史研究的阶段性视角来看,马克思与西方政治哲学关系研究的关键基础在于如何理解马克思与近代自然法权传统的差异性问题。对此,不能如一些现有研究一样,笼统地用“超越论”来回答,而要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自身的理论自觉与理论无意识等多个层面来具体剖解传承性与超越性的复杂纠葛。
首先,从理论自觉层面看,马克思是如何批判近代政治哲学的,他所理解的近代自然法权在何种意义上是自身矛盾的、因而是过渡性的?显然,这依赖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结构的再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层内在联系与浅层外部表现之间、直接生产中的剥削关系与流通分配中的自由平等形式之间存在着客观的矛盾结构。这种矛盾结构的再生产就产生出内在联系与外部表现之间的矛盾形式即剥削性生产关系与简单流通、“三位一体”表象及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生产当事人日常意识之间的对立同一性。要言之,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外部表现的意识形态表达,近代自然法权及正义体系与生产方式内在联系是相互矛盾的,因而其自身就蕴含着社会内容与观念形式的矛盾。由此可见,从理论自觉的层面说,作为自然权利的自由平等显然不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所积极追求的确定性政治价值,而是予以扬弃的中介性、过渡性概念。
其次,从理论自觉层面看,马克思所积极追求的“自由个性”“自由人联合体”,是在何种意义上构成对近代自然法权及正义体系的超越?《哥达纲领批判》对“按劳分配”的价值规律属性和资产阶级(市民)局限性的分析,关于平等权利的不平等后果的悖论呈现,其实质在于对近代法权及正义体系的形式性、空洞性与自反性的历史性批判。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平等权利虽然脱离了它的简单流通基础,然而仍然保留价值规律的形式特征。纯形式的权利一旦推向极致,就会因为缺乏内在实质目的的引导而走向反面。无论权利如何贯彻落实,总是依赖于并包含着自身的反面。对于共产主义的发展来说,资产阶级法权是必经的中介环节,也就是所谓新社会的旧痕迹。初级阶段的共产主义仍然带有资本主义社会的形式性规定。由此,作为历史发展的实质性趋向的自由个性与自由人联合体,必然以按需分配为基础。按需分配中的需要,是历史形成的合理需要、差异性需要,是合乎人的本性的个体性需要,蕴含着自由全面发展之潜能以及这种潜能的再生产。按需分配取代按劳分配,其历史意义在于,从仍然依赖于他者的、形式化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向着从自身出发的、实质化的共产主义发达阶段跃升。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近代法权及正义体系的历史性扬弃是重要的节点。
之所以说自然法权是形式性的,是因为法权是对自由的形式规定,而不是对自由的实质规定。也就是说,法权是从什么束缚中摆脱出来的自由,是否定性的自由,而不能提供自由的肯定性目的即应当去做什么。而能够提供“应当”的这种肯定性自由,只能是道德实践的自律性。然而,道德自律却束缚于内在性、主观性而与外部实存抽象对峙,产生出“应当”与“是”的对峙,因而必然被扬弃而纳入伦理性总体。伦理性总体的客观自由扬弃了“应当”与“是”的对立,使已经存在的规范性生活继续存在,或者说,维持着规范性社会关系的不断再生产。然而,伦理精神最终证明自身是理念主体的自我认识,从而在永恒自我复归中走向自我同一性的封闭圆环。因此,只有将伦理自由重构为多重社会关系的自身超越趋势及其中孕育的差异性能力、复数性需要及个性化自由,才能把握历史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递升的开放性。上述从近代自然权利论到康德、黑格尔再到马克思的逻辑进展表明,规范日益历史化、规范日趋内化于历史进程而达成实质化的一种发展趋势。由此可见,相较于自然法权,自由个性是对人类自由更具实质内容的规定。
最后,从理论不自觉或无意识层面看,马克思是否预设了某些“超历史的”价值规范、自然法权或正义原则?当然,如上所述,马克思有意识地克服经验事实与价值规范、应有之物与现有之物的对立,探求事物之中的理性。将事实与价值的对峙历史地理解为现代资本主义境遇的阶段性产物,并要求从理论方法上克服之,从历史上扬弃之。然而,作为历史内在目的之自由王国、自由个性、最合乎人类本性的活动等,是否蕴含着一种不自觉的超历史的价值规范?
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何种意义上理解“超历史”?这里的“超历史”不能看作独立于历史进程、历史特定性的“超验”,同时,也不能看作构成历史之逻辑前提的“先验”。这里的“超历史”应当被看作内生于但又不局限于历史特定阶段,在不同历史阶段之间构成演进的内部联系与贯穿逻辑,并能够在思维总体中得到合理抽象和具体再现。换言之,超越特定历史阶段而能够被合理抽象、具体再现出来的真实的历史连续性和共同性。自由个性可以理解为这种意义上的“超历史”目的。从后思索地看,自由个性超越了历史阶段性的局限,实际上是贯通历史各阶段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客观趋势,即自由个性首先是趋势,是规律,而后才是价值,是规范。历史首先规定着规范,而不是相反。
重建研究目的
关于研究方向与研究内容的反思,最终都导向了研究目的重建。研究马克思与西方政治哲学关系问题,归根结底不是为了在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哲学之间进行比附与嫁接,而是要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特别是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建构一种面向现实政治实践的政治哲学。
当代政治哲学建构存在着相互对峙的双重路向。一是趋于先验建构的规范主义,无法触及现实的“事实”层面,与之保持抽象对峙。二是崇尚经验确证的实证主义,无法触及现实的“价值”层面,与之保持抽象对峙。这种对峙,经常被理解为各种“张力”。然而,无论是规范主义还是实证主义,都是站在现代性这个凝固不变的“永恒现在”来思考规范与事实的关系,因而只是不断地自我证明或自我再生产出这个规范与事实的二元对峙。进一步地,也就没能提出下列关键问题:为何现代的社会现实似乎总是包含着事实与价值两个对峙的层面?为何只有现代哲人才能提出这一问题?
如果从后思索规范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就能看到其历史的短暂性、过渡性。首先,立足于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即规范与事实的分裂,向过去回溯传统伦理性总体的混沌不分。进而,从过去回望现代社会中规范与事实的二元分离及主体与客体、国家与市民社会、道德与政治等一系列伴生的对峙。而后,从现在向未来预见规范与事实的历史性扬弃,揭示出历史本身的内在目的。由此,才能真正把握住现代社会现实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共时性汇聚,真正在古今之间或之上进行思考。
从后思索引导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能够把握作为历史的“现实”,而规范主义与实证主义只能拘泥于“价值”或“事实”的非此即彼状态。因而深入研究和持续推进《资本论》哲学思想,开显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政治哲学意蕴,是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