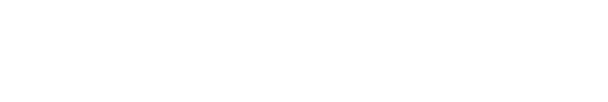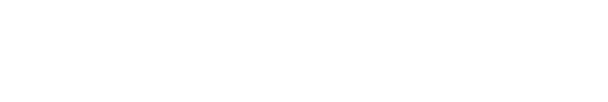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马克思在 1845 年写下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乃至一般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尽管学者们在对《提纲》的思想史定位和具体文本的理解上还有不同观点。但不容置疑的是,这一文献不仅标志着马克思从“以费尔巴哈为中介批判黑格尔”走向了“以批判费尔巴哈为中介建构新世界观”,也标志着马克思的思想发展首次超越了曾经领先于他的恩格斯和赫斯。随后不久,马克思就说服了恩格斯,并且两人合作撰写了正面阐述唯物史观基本观点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并一举奠定了他的“第一小提琴手”之位。
然而,在近来的研究中,有若干学者试图否定《提纲》在思想史上的里程碑性质。他们断言,《提纲》不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提纲,而仅仅是《神圣家族》中的唯物主义思想的延续。据说,这个结论是德国文献学专家英格·陶伯特的最新研究成果,是以科学的版本考证为根据的,因而任何不同意这个结论的“马克思文本解读”,都属于“无视版本研究的新成果”,都是“想象力丰富”的“大胆假设”和“过度解读”!
果真如此吗?本文将通过思想史语境中的文献考证,证伪上述观点。这一证伪,不仅不“无视版本研究的新成果”,相反,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以这些“新成果”为依据的。
一
首先我们来看《提纲》的写作和出版情况。《提纲》写在马克思 1844-1847 年的记事本第 53-57 页上,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发表。1888 年,恩格斯在出版《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时,将《提纲》作为附录首次发表。恩格斯不仅加了标题——《马克思论费尔巴哈》,而且对内容加以修改。这些修改,有些只是文字性的,但有些却是思想性的原则问题(本文作者将另文讨论这个问题)。1926 年,当时的苏共中央直属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 1 卷(法兰克福),其中首次收录了马克思 1845 年写的《提纲》原稿。1932 年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一版(MEGA1)第一部分第 5 卷、1956 年的俄文第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和 1960 年的中文第一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均同时收录了《提纲》的两个版本。但中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版(1972 年)只收入了恩格斯的修改稿,1995 年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二版才添上了马克思的原稿。
在各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上标明的《提纲》写作时间是 1845 年春天。其依据是恩格斯晚年的回忆,“在我看来这一思想(引者按:指的是《共产党宣言》阐述的唯物史观的思想)对历史学必定会起到像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所起的那样的作用,我们两人早在 1845 年前的几年中就已经逐渐接近了这个思想。当时我个人独自在这方面达到什么程度,我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就是最好的说明。但是到 1845 年春我在布鲁塞尔再次见到马克思时,他已经把这个思想考虑成熟,并且用几乎像我在上面所用的那样明晰的语句向我说明了。”因此,恩格斯只是推测在他回到布鲁塞尔之前,马克思就已经完成了《提纲》。
20 世纪 60 年代,巴加图利亚通过对记事本内容、墨水等因素的研究,推测《提纲》可能写于1845 年 4 月 5 日和 7 月 12 日之间。巴加图利亚推测的主要依据是《提纲》在记事本中的位置。他的总假设前提是:材料在记事本中的分布次序就是写下材料的时间顺序。由于《提纲》前面有一个墨水写的书目(44 页)全部是英国的图书馆的书目,而且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字迹交叉写成的,不同于在此之前马克思用棕色铅笔和普通铅笔写的两个书目(36-37 页和 38-43 页),所以这个书目必定写于恩格斯来布鲁塞尔之后。而《提纲》的写作时间也不可能早于恩格斯来布鲁塞尔之后(巴加图利亚认为是 1845 年 4 月 5 日,陶伯特考证为 4 月中旬,MEGA2 为 4 月中旬)。另外,在《提纲》后面也有一个“英国公共图书馆的书目”(74-83 页),显然是在曼彻斯特写下的。巴加图利亚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 1845 年 7 月中旬(巴加图利亚认为是 7 月 12 日,陶伯特认为是 7 月 8 日,MEGA2为 7 月 10 日之前)就启程赴英国旅行了,所以《提纲》的写作时间不可能在此之后。巴加图利亚得出结论:《提纲》的写作时间在 1845 年 4 月初至 7 月初。不过,他仍然认为恩格斯的回忆是正确的。巴加图利亚甚至说,由于恩格斯在晚年手头就握有写着《提纲》的“马克思 1844-1847 年记事本”,因此“1845 春”不是恩格斯凭回忆得出的写作时间。
但问题在于,“春天”这个时间太模糊。从 4 月初到 7 月初,都可以算“春天”。准确的写作时间究竟是什么呢?巴加图利亚认为,文献学事实虽然可以确定,但“要从这些事实中作出明确的结论,还是不可能的”。即便如此,他倾向于 4 月初。其理由是:写有《提纲》第 1 条的第 53 页是以“四行文字”开始的,这四行文字是:
神灵的利己主义者同利己主义的人相对立。
革命时期关于古代国家的误解。
“概念”和“实体”。
革命——现代国家起源的历史。
巴加图利亚认为,这四行文字与《神圣家族》相关。比如《神圣家族》第六章第三节的《对法国革命的批判的战斗》这一小节发挥了第一、二、四行文字表达的思想,而第三行文字在《绝对批判的思辨循环和自我意识的哲学》这一小节中得到进一步发展。鉴于马克思有先做笔记后写著作的治学习惯,所以巴加图利亚认为《提纲》可能是《神圣家族》的准备材料。
巴加图利亚的观点其实是站不住脚的。《神圣家族》早在 1845 年 2 月底就出版了,马克思在 1845年 4 月还去写它的“准备材料”干什么?前东德专家英格·陶伯特更倾向于《提纲》是 7 月初写的,其理由有三:第一,1845 年 6 月 25-28 日之间出版于莱比锡的《维干德季刊》第 2 期上刊登了费尔巴哈的文章《因〈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而论〈基督教的本质〉》,其中费尔巴哈第一次自称“共产主义者”,这是促使马克思阐明自己对费尔巴哈之态度的直接动因。第二,《维干德季刊》第 2 期还刊登了古·尤利乌斯的文章,把马克思说成是“费尔巴哈创立的观点的深造者”,并认为以费尔巴哈和马克思为一方,鲍威尔为另一方,双方的共同基础是“黑格尔的思辨”,《提纲》的写作与这篇文章对《神圣家族》的批判也有关。第三,赫斯在 1845 年 5 月—6 月间写的批评文章《论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小册子《晚近的哲学家》里批判了费尔巴哈,这也促使马克思重新审视他对费尔巴哈的立场。
但我们仔细推敲,就会发现陶伯特咬定“《提纲》应当是马克思在看到《维干德季刊》第 2 期之后写的”,其文献考证上的证据并不确凿。巴加图利亚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说过,“不太可能的是,马克思、恩格斯读了费尔巴哈的文章;更不可能的是,这篇文章是《提纲》的写作诱因。”莱比锡6 月底出版的杂志,马克思 7 月初在布鲁塞尔(去英国前)就看到,是不太可能的。而马克思当时正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研究(记事本中的书目即是证据),同时打算出版“国外社会主义文丛”(见记事本),他怎么可能看到一篇费尔巴哈的文章就随随便便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何况这还是涉及新世界观的重大观点!在国内某些学者眼里,陶伯特关于“《提纲》只可能写在《维干德季刊》第 2 卷出来之后”的观点,就是从科学的文献考证中得出的马克思学“新成果”了。其实,这只是无法证实、却早就被证伪的旧观点。
二
是否看到《维干德季刊》第 2 期上的费尔巴哈的文章,并不是马克思是否写作《提纲》的关键因素。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决不会只是看了某篇文章之后“灵机一动”的结果,而是他从 1844 年夏天开始的经济学研究、哲学研究和社会主义研究互相支撑、互相推动带来的“深思熟虑”的结果。因此,只有放在马克思这一段时间前后的思想转变的大语境下才能理解《提纲》的写作。事实上,巴加图利亚倾向于《提纲》是 4 月初写的,陶伯特倾向于 7 月初,两人都不是从文献考证上得出的结论,而是从文本解读得出的思想史结论!
巴加图利亚比较了《提纲》前 10 条的内容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内容,深入解读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黑格尔现象学的结构》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提纲》第 11 条相关的思想内容,证明《提纲》第 11 条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主旨,而《提纲》中的所有基本原理都可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反映和进一步发展。因此,《提纲》恰恰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提纲。如果说,《提纲》是新世界观的基本原理的第一个文件,那么《德意志意识形态》就是第一次全面制定了新世界观。巴加图利亚还证明: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意图在 1845 年 4 月就已经形成;另一方面,恩格斯 1845年 4 月来到布鲁塞尔后,把费尔巴哈的信转交给马克思,这很可能就是马克思写作《提纲》的直接诱因。
巴加图利亚通过文本解读,判定《提纲》的写作时间是 1845 年 4 月。陶伯特提出不同意见的时候,最主要证据也不是来自文献考证,而来自文本解读。她认为,《提纲》中所有的正面表述,无论是“实践”范畴还是“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都已经包含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中了;而《提纲》的新意在于它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人道主义,这是对《神圣家族》中的唯物主义论题的重述。由此,陶伯特得出结论:《提纲》的写作不是同《德意志意识形态》有关,而是《神圣家族》的延续。换言之,唯物史观形成过程中的重大转折点不是 1845 年春天,而是 1844 年 8 月底,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合作写《神圣家族》!陶伯特甚至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 1843 年底各自独立地完成了向历史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立场过渡”,而“唯物史观的制定工作开始于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几篇文章”。正因为这样,陶伯特才格外看重 1845 年 3-6月间《神圣家族》受到的批判,看重《维干德季刊》第 2 卷上费尔巴哈的文章对《提纲》的诱因作用,才把《提纲》的写作时间定在 1845 年 7 月。这样看来,陶伯特关于《提纲》的“新成果”,根本不是从文献学考证能够得出的结论,而是她“思想史结论”先行,文献考证在后的结果。陶伯特在暂时不能得出准确写作时间的情况下,以她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的理解为依据判断文本的意义。姑且不论陶伯特是否难逃“过度阐释”之嫌,她的研究至少证明了一点:文献考证倘若丧失了思想史维度,就得不出任何有价值的结论。
如果我们沿着陶伯特的思想史思路继续前进,把《提纲》的写作时间向后推到 1845 年 11 月也未尝不可。因为《维干德季刊》第 2 卷上只有费尔巴哈的一篇文章,只有在《维干德季刊》第 3 卷上(1845 年 10 月 16-18 日出版),才形成了一个完全的混战:鲍威尔的文章《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批判施蒂纳和费尔巴哈,批判费尔巴哈“观点的深造者”赫斯、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的作者”),施蒂纳撰文《施蒂纳的评论者》替自己辩解,同时批判费尔巴哈、赫斯及施里加(布鲁诺·鲍威尔的追随者,本名齐赫林斯基),费尔巴哈也写文迎战。马克思、恩格斯在布鲁塞尔看到《维干德季刊》第 3 卷,至少得在 11 月了。
至于巴加图利亚的结论(《提纲》不晚于 7 月初,在 MEGA2 中又说不晚于 6 月中旬),一来他自己也只是说“可能”,没有说是最终结论(他反而说,最终结论是“不可能的”);二来,他推测的总假设前提并非无懈可击,材料在记事本中的顺序并不一定严格等同于写作的时间顺序。记事本中许多书目后面都有空白页,这说明有可能先写下后面的内容,再把前面的书目写完。巴加图利亚不得不承认,记事本中已经包含了许多例外。因此,虽然《提纲》后面的书目是在英国写的,但不能证明《提纲》在马克思去英国前就全部写完了!很有可能的一种情况是:马克思写了《提纲》的第 1条(或前面几条),然后空出若干页,开始写法国的书目(记事本 58-70 页),随后又陆陆续续将《提纲》写完。
这一推测至少有以下几个旁证:第一,整个《提纲》的标题“Ⅰ)关于费尔巴哈”和提纲第 1条(记事本第 53 页)的编号直到在写第 2 条(记事本第 54 页)的时候才加上,说明《提纲》已经不是“一气呵成”的。因此,后面的一些条文有可能是在马克思看见《维干德季刊》第 2 期上的文章之后(7 月以后)写的。第二,《提纲》的第 11 条之前有一道横线,把第 11 条和第 10 条分隔开来。这也说明《提纲》很可能不是一次写成的。第三,根据燕妮·马克思的回忆,马克思、恩格斯在 1845年夏在酝酿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而《提纲》正是其“准备材料”。
三
《提纲》究竟写于何时?并不单纯是文献考证问题,而且是一个思想史问题,关于写作时间的判定与人们对《提纲》内容的不同判读息息相关。巴加图利亚认为《提纲》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提纲(不是写作提纲),因此它是 4 月初写的。陶伯特认为“《提纲》的写作与《神圣家族》的反响有关”,所以认为它是 7 月初写的。我们基于《提纲》和《神圣家族》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史联系,提出《提纲》写于 1845 年 4 月到 11 月之间的推测。
这里不能不提陶伯特得出她的结论的主要文本根据——马克思写在《提纲》前面的“四行文字”。严格说,这不叫“四行文字”。在陶伯特参编的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538 页上,编者加上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标题。在英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上,编者加上了《笔记本中的札记》的标题(中文第一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也是这个标题)。我们现在姑且将错就错,继续称之为“四行文字”。巴加图利亚说得好,不解决“四行文字”问题,就不能阐明《提纲》的历史地位和意义。
显然,“四行文字”涉及《神圣家族》。巴加图利亚说《提纲》是《神圣家族》的准备材料,闹了个笑话。陶伯特断定《提纲》的写作与《神圣家族》引发的争论有关,倒是有一定的依据。巴加图利亚已经说明《对法国革命的批判的战斗》这一小节与第一、二、四行文字有关,其实,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第六章第三节写的《对法国唯物主义批判的战斗》这一节正对应于第三行文字“‘概念’和‘实体’”。这一小节开头就谈到斯宾诺莎的“实体”,然后指出鲍威尔把法国唯物主义叫做“法国的斯宾诺莎学派”的说法来自于黑格尔,黑格尔的“哲学史”把法国唯物主义说成斯宾诺莎的实体的实现,而“鲍威尔先生还可以从黑格尔那里知道:如果实体不在其进一步的发展中过渡为概念和自我意识,那它就会成为‘浪漫主义’的财产。”陶伯特也大量引用《神圣家族》的文本,以证明“对法国的和英国的唯物主义以及对英国的和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研究”是“唯物史观形成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但是,上述文本依据充其量不过说明了“四行文字”和接着“四行文字”的《提纲》是《神圣家族》论法国革命与论法国唯物主义等两个论题的延续。然而这并不足以否定《提纲》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联系。在对法国唯物主义的评价和对费尔巴哈的评价上,《神圣家族》和《提纲》在理论主旨、立场、观点和方法上都截然不同。从理论主旨上看,从《神圣家族》对法国唯物主义和费尔巴哈的双重肯定转向了对法国唯物主义和费尔巴哈的双重批判。《神圣家族》赞扬法国唯物主义而批判 17 世纪的形而上学;赞扬费尔巴哈,认为只有他才“从黑格尔的观点出发而结束和批判了黑格尔的哲学”。而《提纲》第一条已经批判旧唯物主义,所谓“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首先指的是法国唯物主义,其次才是“包括费尔巴哈在内”。《提纲》第三条也批判了法国唯物主义中的“环境决定论”、“教育决定论”。从哲学观点上看,《提纲》第一条表明,旧唯物主义,不管是法国唯物主义还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都不再像《神圣家族》中那样,被马克思认为是超越形而上学,高于唯心主义的东西。从政治立场上看,《神圣家族》认定法国唯物主义“直接成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财产”,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哲学基础,费尔巴哈的人类学则为德国的哲学共产主义奠定基础;但是,《提纲》第十条已经讲“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显然把它们视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这里的评价已经完全对立于《神圣家族》,而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的理论“同正在进行斗争的而尚不发达的资产阶级相适应”的看法,以及关于费尔巴哈“和其他的理论家一样,只是希望达到对现存事实的正确理解,然而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却在于推翻这种现存的东西”的批判相一致。
总之,紧挨着《提纲》前面的“四行文字”虽然延续了《神圣家族》中关于革命、唯物主义、社会主义等论题,但是其理论目的、哲学观点和政治立场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事实上,陶伯特本人也承认,《提纲》“明确指出了全部旧的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主要缺点,并且确认旧的唯物主义代表市民社会,这些在《神圣家族》中都没有出现。”这样来看,与其说“四行文字”是《神圣家族》的延续,不如说是对《神圣家族》的否定和超越。陶伯特试图以“四行文字”与《提纲》的文献学联系来证明《提纲》是《神圣家族》的延续,恐怕要“竹篮打水一场空”。
四
其实,《提纲》与“四行文字”的关系仅限于“四行文字”和《提纲》第 1 条写在同一页上,并且“之间没有明显的间隔”而已。两者并不是在同一个时间写下的。陶伯特认为,“四行文字”和《提纲》是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试图建构的“现实的人道主义”遭受批评之后的产物。鉴于人们把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人道主义的观点和“德国哲学的社会主义”的观点强加给马克思和恩格斯并因此谴责他们,但《德法年鉴》和《神圣家族》并不持有这样的观点,所以马克思才去写《提纲》。在她看来,既然《提纲》仅仅是马克思对鲍威尔在《维干德季刊》第 2 期上的文章所做的反应,那么《提纲》就只是《神圣家族》中唯物主义思想的延续,而不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提纲”。(毫无疑问,她的意思是指“思想提纲”,因为《提纲》不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提纲,是一目了然的事情。)
事实上,陶伯特不过证明了她力图否定的观点。正因为鲍威尔、施蒂纳、费尔巴哈之间的这场混战与赫斯以及“《神圣家族》的作者”有关,因此《提纲》才恰恰构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提纲”(当然是指“思想提纲”)。这是因为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最初动因是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1844 年 11 月出版),但直接动因恰恰是鲍威尔在《维干德季刊》第 3 期上批判费尔巴哈与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文章。马克思、恩格斯被迫迎战,为的是表明自己的新世界观,与费尔巴哈、鲍威尔等人划清界限——与鲍威尔划清界限的任务,《神圣家族》已经完成;与费尔巴哈划清界限的任务,私下里已经由《提纲》完成,但公开著作还没有,于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应运而生。如前所说,按照 MEGA1 版编者维列尔和巴加图利亚的考证,马克思、恩格斯在看到《维干德季刊》第 3 期后,首先不分章节地批判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即《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卷第一章《费尔巴哈》的“主手稿 ”(马克思在手稿上编的页码是 1-29 页),然后再分出专门批判鲍威尔的第二章《圣布鲁诺》和专门批判施蒂纳的第三章《圣麦克斯》。这就证明了《神圣家族》及其之后的争论构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的动因,也恰恰证明了《提纲》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提纲。
即使按照陶伯特的“最新考证成果”,这个结论也同样成立。陶伯特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顺序是这样的:1845 年 11 月底到 12 月初,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以一篇驳鲍威尔和费尔巴哈的论战文章来实现他们对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批判,而且这篇文章还“包含对自己的历史理论的阐述”。写一本名为《莱比锡宗教会议》的小册子批判鲍威尔、施蒂纳和卢格的计划,则是在这项工作的下一个过程才产生的。最终,放弃了批判卢格的计划,并从批判鲍威尔的《圣布鲁诺》中抽出一部分构成“主手稿 I”(1-29 页),从批判施蒂纳的《圣麦克斯》中抽出一部分构成“主手稿 II”(马克思编的第 30-35 页),抽出另一部分构成“主手稿 III”(马克思编的第 40-72 页),这样组成了第一章《费尔巴哈》的主体部分。简单说来,按照陶伯特的思路,有了《维干德季刊》第 2 期,才有《提纲》(所以它是 7 月初写的);有了《维干德季刊》第 3 期,才有《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提纲》在思想上是离《德意志意识形态》更近还是离《神圣家族》更近,结论不是很明显了吗?
《提纲》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侧重点虽有所不同,但根本任务是一致的,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清理自己以前的世界观、总结自己的思想演进成果(新世界观),并深化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而写下的。因此,和陶伯特把马克思发表于 1845 年 11 月 20 日的《答布鲁诺·鲍威尔》一文编入 MEGA 第一部分第 5 卷(《德意志意识形态》专题卷)的做法相比,巴加图利亚要求将《提纲》编入第 5 卷的建议更“科学”。顺便提一下,巴加图利亚的编辑思路延续了梁赞诺夫的传统;而陶伯特的“马克思学”编辑新思路不但与梁赞诺夫的所谓“苏联马克思学”格格不入,反倒和斯大林时代阿多拉茨基主持下的 MEGA1 编辑思路不谋而合。其中缘由,令人深思。